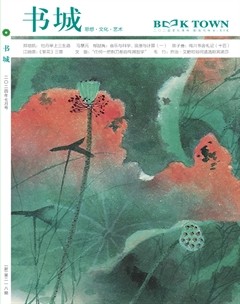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古代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一样,以米饭和面饼为主食。
米饭
无论是米饭,还是面饼,都来自谷物。那么,古代中国人食用哪些谷物?《黄帝内经》大概是战国时的一本医书,后成历代医家经典,其中说道:“五谷为养,谓黍、稷、稻、麦、菽,以供养五藏之气。”意思是说,“五谷”,即黍、稷、稻、麦、菽,可以供养“五藏之气”。“五藏”即“五脏六腑”中的“五脏”。可见,这里的“五谷”是主食,吃了可以活命。黍、稷、稻、麦、菽,其中的稻和麦,我们今天比较熟悉,黍、稷、菽又是什么?其实,这三种东西我们并不陌生,黍就是黄米,稷就是小米,菽就是豆。看来,战国时代的中国人吃的主食,和今天没多大区别,也是那么几种。只是,他们的吃法,还有哪种吃得多、哪种吃得少,却和我们大不相同。
《礼记》中则写道:“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和《黄帝内经》所说的“五谷”比较,前面三种是一样的,都是黍、稷、稻,后面说到了粱,却没有了麦和菽。粱,也就是粟,一种上好的稷(小米)。古书中有“膏粱子弟”一说,指的是吃着肥肉和细粮的富家子弟。至于后面的白黍、黄粱,并不是其他谷物,是指上好的黍和粱。至于稰和穛,按照为《礼记》作注的郑玄所说“熟获曰稰,生获曰穛”,即晚熟的谷物称作“稰”,早熟的谷物称作“穛”。也就是强调,无论是晚熟的,还是早熟的,都要用好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礼记》讲的是“礼”,它说到的“饭”,不是平时吃的饭,而是用来祭祀的饭。所以,要用好的黍、稷、稻。至于它为什么不提“五谷”中的麦和菽,那是因为麦和菽在当时很罕见,连诸侯也未必吃得到。
请看《礼记》中的另一段话:“饭之品有黄黍、稷稻、白粱、白黍、黄粱……此诸侯之饭,天子又有麦与菰。”可见,麦和菰在当时弥足珍贵。菰是什么?菰是一种菽,就是茭白的种子,因为长得很小,很像米,所以被称作“菰米”或者“茭米”。
那么,黍、稷、稻在当时又是怎么吃的?主要是蒸来吃的。这可以从一本叫《逸周书》的古书中得到证实:“黄帝作井,始灶,烹谷为粥,蒸谷为饭,燔肉为炙。”这里说,挖井、筑灶始于黄帝,说黄帝开始“烹谷为粥,蒸谷为饭”。“烹”,就是放在水里煮。关于“蒸”,其实,当时的蒸和后来的蒸是不一样的。当时还没有蒸锅和蒸笼,而是用一种叫“甑”的陶器来蒸饭的。至于“燔肉为炙”—“燔”就是烤,“炙”就是熟肉。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古代中国人何时开始“烹谷为粥,蒸谷为饭”的。其实,谁也说不清,因为谁也不知道“黄帝”究竟是何时之人,或许根本没有此人,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不过,我们虽然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前”是怎样的,却知道后来数百年间,古代中国人就一直“烹谷为粥,蒸谷为饭”。当然,在这期间,“蒸谷为饭”的方法一定是有所改进的,但我们无从得知,因为这期间的古书里没说。
直到东汉以后,西晋有个叫周处的大官,写了一本叫《风土记》的书,其中才写到如何“蒸谷为饭”:“精折米,十取七八,取淅使青,蒸而饭,色乃紫绀。”文中的“米”,是粟米,即小米。那么,什么叫“折米”?折米,就是淘米,去掉米中的杂质。文中说“十取七八”,可见当时的米实在不怎么样,竟然要“折”掉四分之一。“取淅”,即清洗。
周处是做大官的,肯定不会下厨做饭,他这段话说不定是从哪里听来的,而且也太简单了。
不过,北魏期间,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里面讲到“作粟飧法”,比较详细:
舂米欲细而不碎,碎则浊而不美。舂讫即炊,经宿则涩。淘必宜净,十遍以上弥佳。香浆和暖水浸饙,少时,以手挼,无令有块。复小停,然后壮。凡停饙,冬宜久,夏少时,盖以人意消息之。若不停饙,则饭坚也。投飧时,先调浆,令甜酢适口。下热饭于浆中,尖出便止。宜少时住,勿使挠搅,待其自解散,然后捞盛,飧便滑美。
这段话中,“饙”,意思是蒸,而且是专指蒸饭。“挼”,意思是揉。“复小停,然后壮”,就是再等一等,然后“壮”(猛蒸)。“凡停饙,冬宜久,夏少时,盖以人意消息之”,就是“停”和“饙”的时间,冬天长一点,夏天短一点,看情况而定。“投飧时”就是吃的时候。“浆”就是汤。“尖出”就是(饭从汤中)冒出。“宜少时住”就是最好再等一会儿,等饭粒自行“解散”后,再捞出来吃,吃起来“滑美”。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那时的小米饭,其实是泡饭,而且是甜酸的。在其后的数百年间,古代中国人就是吃这种饭的。所用的谷,主要是黍和稷,即黄米和小米。稻米吃得很少,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即中原诸国),天气较冷,水源较少,水稻种得很少,产量也不高。
不过,在西汉时还被认为是天子吃的“麦”与“菰”,到了北魏(与东晋同时),好像已变得很平常了。因为我们在《齐民要术》中读到了“作面饭法”和“菰米饭法”。《齐民要术》旨在“齐民”,显然是针对民间的。
魏晋之后,是南北朝。这期间,找不到任何关于“做饭”的记述。我们只能假定,情况没多大变化。于是,就到了唐朝。唐人固然也吃小米饭,偶尔也会吃稻米饭(当然都是蒸来吃的),但他们更喜欢吃“饼”(后文讲到“饼”的时候再作解释)。
唐人喜欢吃“饼”的习俗,无疑会传至宋代。不过,宋代人口比唐代多了许多,而且就是在宋代,汉族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也就是所谓南方人,是以米饭为主食的。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吃米饭的,只是在宋代之前,以吃“饼”为主的北方人一直把他们视为“南蛮”。
很可能,蒸饭变为煮饭,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因为很可能,那些南方人本来就是把稻米煮来吃的,从未蒸过,也从未有过“甑”这种陶器。为什么说“很可能”,因为学术界至今无法确定,古代中国人是何时改蒸饭为煮饭的。
如果这事发生在宋代,那么对于南下的中原人来说,放弃蒸饭而接受煮飯,可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到了清朝的乾隆年间,我们仍从袁枚的《随园食单》中读到关于蒸饭和煮饭的议论:
《诗》称:“释之溲溲,蒸之浮浮。”是古人亦吃蒸饭。然终嫌米汁不在饭中。善煮饭者,虽煮如蒸,依旧颗粒分明,入口软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