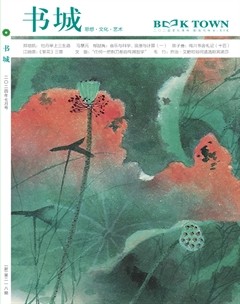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卫风·伯兮》
谖,忘也。《诗经》中出现过三次“谖”,恰巧都在《卫风》中。卫国是殷商文明的旧地,周武王灭商之后,周公旦封其弟康叔于此,建立卫国,定都朝歌,历经西周东周和春秋战国九百年,至秦二世,是周王朝生存时间最长的诸侯国。漫长的时间意味着记忆、历史和遗忘。《淇奥》“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考槃》“独寐寤言,永矢弗谖”,都是在强调不可忘记,唯有《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却似乎在表达,有时候,面对无可奈何的失去,遗忘之术与记忆之术同样珍贵。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可能是这位男子的字,在这里当是妻子对丈夫的私称。起句的“朅”(读“切”声),流行的解释是“壮健英武貌”,这个解释的源头是《毛传》,但除了《诗经》注疏之外,这个“朅”字在早期古典诗文中从未被如此应用过。《说文·去部》:“朅,去也。从去,曷声。”段玉裁注:“古人文章多言朅来,犹往来也。” 如《左思·蜀都赋》“殆而朅来”,李白《禅房怀友人岑伦》“朅来已永久”,都是明例。最靠近国风创作时期的《楚辞·九辩》中有“车既驾兮朅而归”的句子,蒋天枢《楚辞校释》解释这句为:“已去而又复返,欲再见王有所白也。” 朅即作“去”解,陈子展又认为,“今楚语犹谓去为朅”,这是把“朅”视为“去”的方言变体。总之,将本义为“去”的“朅”字解释为“壮健英武貌”,唯见于诗经注疏系统,这就特别让人生疑了。
王先谦根据三家诗的韩诗钞本,认为“朅”当作“偈”或“傑”,程俊英进一步弥补说“朅”可能是“偈”或“傑”的通假字,都是在为《毛传》的解释曲意回护,并没有多少文献学上的佐证。再者,若作“偈”或“傑”解,就与后句“邦之桀兮”的“桀”在意思上重复了,虽然有的论者认为意思重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属于古书中的“义同字变例”,但从诗的角度,诗三百中几乎没有为了重复而重复的句子,即便看似重复,其中也都有其微妙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中蕴藏的不可含混带过的准确,恰恰就是诗之为诗的部分。
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朅,《说文》云,去也。言去从役也。”《说文:去部》:“去也,人相违也。”人与人相互离开,这就是“去”。按照这个遵从本义的朴素解释,首句的意思就是,“伯啊离开了啊,国家的俊杰啊”,这显然比“伯啊壮健英武啊,国家的俊杰啊”的表达要更丰富。
再者,从句法结构的角度考虑,《诗经》中但凡“甲兮乙兮” 的句法,几乎都是并列和重复结构,如果把“朅”解释成“壮健英武貌”,它和“伯”之间就无法构成一个并列结构。《诗经》中和“伯兮朅兮”句法最接近的,是“绿兮衣兮”,而后者的“绿”和“衣”其实也可以视为一个并列结构,即“绿色的啊,衣啊”(参陈子展《诗经直解》),表明一块布料的颜色及其用途的并列。而如果按照“朅”的本义“去”来理解,伯的存在和伯的离开就依旧可以构成一个清晰的并列结构,仿佛在表明,他的不在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空洞般的存在。
但还有一个疑惑,既然“朅”本义为“去”,那为什么这首诗中不直接说“伯兮去兮”呢?押韵自然是一个考虑,但在押韵之外,我觉得还可以更进一步,“朅”这个字本身应当视作“去曷”的会意,即“去何处”,而从音韵上讲,如果我们快读“去曷”两个字,就会形成“切”声。陈子展说的楚语读音,或许正是连读的产物。如此,首二句就变成一个更为丰富的问句,“伯啊去哪里了啊,国家的俊杰”,而作为一个回答,后面两句“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就显得特别自然,“伯啊挺着长殳,做着国王的前驱”。
“伯”,是夫君;“邦”,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诸侯之国;“王”,则是这个诸侯国的统治者。这首诗的首章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政治生活的画面,仿佛古典版的送夫从军,但诗人到此为止,接下来,将抒情的重心完全扭转到私人生活的场域。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二章的这几句诗非常有名,历代都有诗人效仿,如徐幹《室思》“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杜甫《新婚别》“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起来慵自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