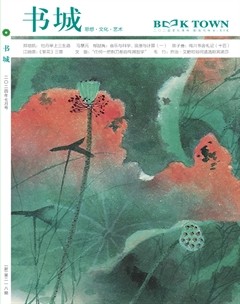2024年3月21日、22日,围绕“音乐与科学,浪漫与计算”的话题,《一点五维的巴赫:音乐、科学和历史》一书作者马慧元,分别与郁隽、范昀、林晓筱、罗逍然四位青年学者展开了两场精彩对谈,本刊拟分两次刊登。
——编者
马慧元:我过去写的书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在作曲家、作品、演奏、乐器,还有音乐跟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关系这些话题。但大约六七年前,我的兴趣突然就转变了。这本书(《一点五维的巴赫:音乐、科学和历史》)风格也好,写作的方法或者思维的框架也好,跟我之前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自以为我对音乐的兴趣还是在的,但是我更愿意去引入一种新的方式去看音乐,我想了解的是音乐“how it works”,它的背后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物理学、数学在支持它?从这个出发点我就去思考一些问题。另外我也找了很多资料,你可以看到在音乐世界里有很多谈论数学和音乐、神经科学和音乐、物理和音乐,还有数学、物理和乐器制造的书籍。但是我看了很多书之后,我的想法又有了一些改变,我觉得跟我的初衷不太一样的是,我现在更感兴趣的可能是科学和音乐没那么有关系的地方。作为一个程序员,我的思维总是会从正反两方面去看问题,如果我想讨论音乐和数学的关系,那么我也会看数学有没有受到音乐的影响,我也会看音乐还受没受到其他事物的影响,到底数学和科学谁对音乐的影响更大;我也会看数学对其他的艺术有没有影响,它对其他的艺术的影响,跟音乐相比,对哪方面的影响更大。这几年读书也好,思考也好,我是没有结论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会有很多想法,在这个过程中想到一些问题,算是一些总结和交流。
首先谈到音乐和数学的关系,我听到一些说法是音乐是数学的一部分,这个成见是从哪儿来的?最早是毕达哥拉斯,他发现了弦长跟音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关系,你把弦长两端固定做一个简单的模型,拨这根弦,它出来一个基音;把弦长缩短到一半的时候,是高了八度的音。大家发现,这么简单的数字关系,却揭示了我们听觉喜欢的和谐,真的是非常惊人。这里就有它的神学和神秘意义在。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很多人都认为音乐就是数学的一部分,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个结论也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的认知肯定都复杂化了,数学变得更复杂了,音乐也变得更复杂了,所以渐渐到了一个程度,两者似乎是在十九世纪渐行渐远了。
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对音乐的传播有着巨大的作用,我想这个传播也会影响到音乐的作曲和演奏,两者似乎又有点回到一起了。但是这个关系跟早期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思考和阅读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包括这本书中提到的,在思考音乐和声波的关系时,有一个著名的法国科学家傅里叶。他发现的傅里叶级数就是把声波怎么分解成我们正弦余弦的表达式,其实并不仅仅是声波,所有的波动都可以用傅里叶级数来表达,甚至世间万物都可以用傅里叶级数来表达。可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傅里叶跟贝多芬就差两三岁,傅里叶发现的声波对我们对音乐的认识有革命性的影响,那他对贝多芬的音乐有多少影响?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没有影响。傅里叶级数一百多年以后才逐渐被音乐家认识和接受,也许到现在都没有被完全接受。一个同时代人对音乐的认识有这么大的贡献,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革,但是对音乐家的音乐生活却没有任何影响。
但另外一个同时代人,拿破仑,他对贝多芬有多少影响?太多了!贝多芬的交响曲跟拿破仑有直接的关系,拿破仑对当时世界的改变,对大家生活观的改变,对贝多芬的音乐都是有直接影响的。所以说到底是什么在影响音乐?数学和科学可以影响音乐,但在很多时候它们的影响远远比不上社会和政治带来的影响。我们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讲。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数学跟艺术的联系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密切,数学和音乐在某些节点上是有相遇的,但是也可能仅仅就是偶然的相遇,甚至可能不相遇也是可以的。
刚才我们说到毕达哥拉斯,他提到了弦长比的关系,被用在调律上。调律必须用到算术,音乐跟数学确实是有联系的,八度我们都要满足1/2的关系,五度要满足2/3的关系,三度要满足一定的关系,4/5也好,7/8也好,这些关系都要满足,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有理数是没法达到这个要求的。因为音程是八度,五度往上走,在某一个点也会跟八度相遇,但最后相遇的时候它会差了一点点。在毕达哥拉斯的时候没有无理数的概念,这个差一点点让大家非常痛苦。我们怎么才能调律调到各种音程都觉得比较舒服,甚至不需要所有的音程都很舒服,哪怕我只有五度和八度同时调准了也行,结果发现五度和八度在各个音程上的同时准确也满足不了。最后的结果就会有一个取舍,要满足这个就不满足那个。但是大家都是认为八度是最重要的,所以最后就以八度為准,所谓的绝对平均律,任何一个间隔都均分,五度、四度都不那么好听,都差一点点,但是听上去还凑合,而且这样任意的间距都能够满足我们所期待的这个五度和四度、三度的关系。从这一点来说,音乐跟数学本质性的联系就是它生命的周期性。无理数这个东西可以在我们生活中无所不在,我们所遇到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无理数,但是它只有在音乐上显得那么尖锐,这个确实也跟我们生理性有关系。在调律的时候正好差了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就是你最痛苦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音乐才跟数学显示出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个紧密的关系也体现在乐器制造上,几种乐器在合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取舍。
但是调律以外,音乐和数学还是渐渐分开了。有一个误会我经常听到,大家都说巴赫是音乐家中的数学家。很多了解巴赫音乐、看过巴赫的谱子的人,会看到他音乐中的对称性、逻辑性,但我不知道所谓的数学从哪儿来。巴赫本身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他是不可能了解很多数学知识的,我这本书里有篇文章讲到,巴赫的儿子中确实有一位是真懂数学的,就是他的长子威廉·弗里德曼,他在莱比锡大学读了数学学位。除了他以外,巴赫家族中没有人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也没有人跟数学和科学产生过任何的联系。巴赫生活的时代,科学机器这些东西确实是在发展,有的人说肯定是对巴赫有一定影响,这个也是对的,我相信总是有影响的,但是巴赫本人并没有体现出这种影响。巴赫有一些风格的变化,其实是跟当时的教会有关系的。
所以,这就说到我这本书的名字为什么叫“一点五维的巴赫”。在我眼里,巴赫的音乐不是数学,但是他的音乐充满了数字。为什么叫一点五维?是因为我们数学中有一个分形的概念,复杂结构有一个可以自相似。但是分形并不限于自相似,它可以自相似,大家都看到过锯齿形状,例如一片叶子,它再长出来一个小叶子还是那个形状,可以无限分下去。这个不光是看着好玩,它有一些很实际的用处。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复杂结构,但复杂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用长度、面积和体积来计算,科学家寻找它们中间的共性,试图把它们联系到一起。最后科学家真的发现了一个奇迹般的规律,就是所谓的3/4理论(Kleiber’s law)。不光是动物,所有的生命体,它质量的3/4次方跟新陈代谢都有正比的关系,B = βM3/4(B是基础代谢率,M是质量,β是常数)!人类最终发现了表达这种复杂结构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分形。“一点五维”仅仅是分形应用中的一个实例。一个三角形,我把这个三角形中间分成四个小三角形,把其中一个抠掉之后,剩下三个三角形,如果它是有质量,就是总质量的1/3;再把一个小三角形中间扣掉,它还是1/3的关系,这个关系就说小三角形的高相当于是大三角形的1/2,但是它的质量相当于大三角形的1/3。这个就不是我们习惯的一维二维三维的比例了,最后我们取下的对数就是1.58倍。这就是“一点五维”的由来。巴赫音乐中体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关系,这个复杂的关系可以说对一些数学关系有一定的隐喻。
但是另外有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巴赫的作品伟大。大家都知道巴赫的音乐首先是很好听的,这是最根本的。有一个瑞典的研究者,她做了非常令人佩服的研究。她发现巴赫很多大型作品,甚至《b小调弥撒》,小節数都是一千四百小节,好多大作品,最后的小节数都是整数,而且它们都凑成了倍数,或者是体现了一定的比例,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但大家再做研究又发现所谓的巴赫整数的理念,并不是巴赫所特有的,当时很多作曲家都有,只不过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其实就是因为巴赫的音乐太有意思了,才引导大家从各个角度去了解他的音乐,包括发现他音乐中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