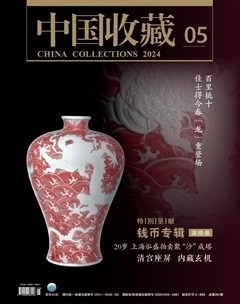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鲜红釉、宝石红釉是霁红瓷器的主要品种,其勃兴正伴随着大明王朝的兴盛,嘉靖时霁红的停烧则预示着明王朝的转折(图1)。因此,霁红瓷的烧造曾被视作与国运息息相关。诚然,瓷事亦国事,瓷器烧造背后与当时的科技发展与财力不无关系。而除了明代,霁红瓷器的“神预言”其实也在清代几乎重演了一次。



这种红令清宫追仿
明代嘉靖時期,曾经名噪一时的鲜红釉瓷器在皇家御窑厂的烧造已难以为继,以致“嘉靖三十六年,上取鲜红,造难成,御史徐坤奏以矾红代”(据《浮梁县志》)。矾红釉是一种低温红釉,虽然容易烧造,但效果不能与高温的鲜红釉同日而语,明代高温铜红釉自此断绝。
朝代更迭,时至康熙二十年(1 6 8 1年),国家基本从战乱中平复,景德镇御窑厂也终于恢复烧造,是为“ 臧窑”。此时御窑所产瓷器基本延续了明末清初以来的青花、五彩、素三彩、青釉、酱釉等民窑品种,仅有豇豆红一项为创新之作。有一种说法是,豇豆红是御窑厂尝试恢复永、宣霁红釉的产物,只是由于技术原因,颜色不能烧至均一,常常出现绿色苔点,反而造就了一时名品,成为一种特殊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品种(图2)。
而霁红釉的真正恢复要待到康熙晚期。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 5年至171 2年),郎廷极任江西巡抚,期间烧造了著名的“郎窑”。由于郎氏富收藏,“郎窑”从而有条件遍仿明代御瓷名品,颜色纯一的霁红釉瓷器也终于得以恢复。此外,“郎窑”在恢复高温红釉的过程中还创烧了著名的郎窑红,康熙朝高温铜红釉一时盛况空前(图3)。
雍正五年(1727年),御窑厂进入常态化烧造的阶段,此时由年希尧督管,是为“年窑”。霁红工艺在御窑得到传承,并被美誉为“年红”,自此霁红成为清宫用瓷的常规品种。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中总结了雍正御窑名品,曾说道:“仿宣窑霁红,有鲜红、宝石红二种”,正说明了清代霁红的渊源所在。雍乾盛世,霁红是颇受皇家追捧的,御窑所产各种霁红琢器造型丰富,常见的霁红盘、碗也有大小数十种之多,并且霁红制品普遍质量较高,红色鲜艳、均匀,诚为盛世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