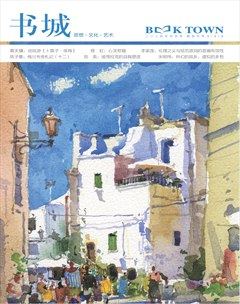我在日本供职的大学有个海外研修制度,教员可休上一年多的学术长假,我的两次长假都选在了捷克布拉格的查理大学。利用休假机会,我于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查理大学国际汉学中心对汉学家罗然(Olga Lomová)教授进行了一次访谈。
罗然研究中国古代诗学、中国文化史、中国二十世纪初叶之思想转变及中国现代文学,著有《大地的讯息—王维诗中的自然表象》(Poselství krajiny. Obraz přírody v díle tchangského básníka Wang Weje)等著作。罗然乃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的再传弟子,我们的话题就从普实克所著《中国,我的姐妹》(Sestra Moje Čína)开始。普实克曾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在中日两国游学,此番东亚之行为他日后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该书一九四○年在捷克出版,细腻生动地记述了普实克的在华见闻。罗然说普实克虽然在书里写到了冰心,其实当年与冰心来往甚少,后来在回忆录里也说他在冰心面前不太敢讲话。与普实克一样,罗然也喜欢做翻译,译过《史记》《茶经》等典籍,还译过《三侠五义》那类古代通俗小说。《史记》捷译本曾获二○一四年查理大学优秀著作奖。她说《史记》印得很漂亮,但卖得并不好,年轻人觉得太难。听她说到年轻人,我就问起捷克大学里中文学习的情况,她回答说:“学习汉学每一代学生都有不同的希望、不同的追求,但学生人数一直变化不大。问题不是本科生,问题是—全欧洲普遍的问题,不只是中文和汉学的问题—本科毕业后读硕士的人越来越少。”
从罗然教授的汉学因缘谈到了捷克文学,还说到语言和翻译问题。我们双方都对对方的母语文学有着浓厚兴趣,但她是汉学专家,我对捷克文学恐怕还没有超过普通读者的认知,听她娓娓道来,仿佛穿过一道道门廊,一步步往里边走了进去。
《外祖母》《五月》
话说从头,罗然最初的梦想是当画家。她笑说这梦想早就没有了,现在只偶尔给孙子孙女画点小动物什么的,好玩儿而已,并不保留。问及最初的文学渊源,罗然提到了涅姆佐娃(Božena Němcová,1820-1862)的长篇小说《外祖母》(Babička),还有马哈(Karel Hynek Mácha,1810-1836)的叙事长诗《五月》(Máj)。
由于母亲病重,罗然从小就在服兰诺(Vranov nad Dyjí)小镇与祖母一同生活。六岁时偶然从祖母的书架上拿出了一本书—随随便便拿出来的,就看进去了,那本书便是涅姆佐娃的《外祖母》。她说:“我马上就把自己的故事与小说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一个女孩子和她祖母的故事,虽然两位祖母不太一样,生活环境也很不一样。”她也看涅姆佐娃写的儿童故事,“都是用小说家的笔法改写成的、比较长的民间故事,不像现在的儿童故事,现在的儿童故事非常简单”。她还阅读翻译成捷克文的外国小说,有什么看什么。六岁的她发现了生活与文学的关系:“生活不是直接印在文学里,文学和生活是两码事;但尽管是两码事,文学还是能够表达出生活中更深刻的意义,表达出从生活表面看不出来的真理。”
涅姆佐娃在捷克文学史上举足轻重,被称为捷克现代散文的奠基人,五百克朗纸币上就印着涅姆佐娃的肖像。罗然说涅姆佐娃在《外祖母》以及其他小说里描写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状态及人际关系,“人都是好人,偶尔也有一些坏人,但总的来说那是个非常和谐的、非常能够共生的世界”。谈到涅姆佐娃的魅力,罗然最推崇的就是她的语言:“她的语言特别美,很适合朗读。翻译成外语她的故事相当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怎么这么简单?”我看《外祖母》中译本时的确觉得有些意犹未尽,原来那语言的韵味被翻译冲淡了。罗然还说在涅姆佐娃的时代当作家—尤其是女作家—非常不容易,体面女性不能随便工作,出门工作就会被人看不起,但涅姆佐娃无视贫穷与白眼,一心追寻理想,“她个人的故事非常感动捷克人,她是最受崇拜的捷克作家”。说到涅姆佐娃肖像上了纸币,罗然颇不认同,认为这对一位贫穷的女作家来说不太合适。
罗然说涅姆佐娃是在讲德语的环境里长大的,修养皆来自德语,并非从小就说捷克语。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一部分捷克知识分子发起了复兴捷克语及捷克文化的运动,她深受影响,主动学会了捷克语并开始用捷克语写作。罗然强调这种复兴运动本来主要是文化行动,并非政治行动。
《外祖母》是捷克学生的必读书。罗然六岁时爱读,成年后再读依然喜欢,说“这是我真的喜欢的一本书”。小学一年级时除了《外祖母》,她还爱读马哈的叙事长诗《五月》。她说其实《五月》对小孩子来说是很可怕的,但描述得异常生动,看不太懂故事也能捕捉到一些意象:“有一個人在监狱里等着他自己第二天被杀……那情景直到现在都记得,我一辈子都怕监狱,不要坐牢!这些恐怖的意象我记得非常清楚,小时候看过的一辈子都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