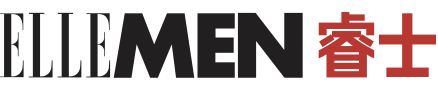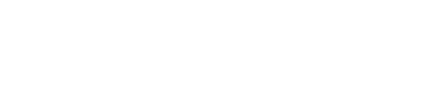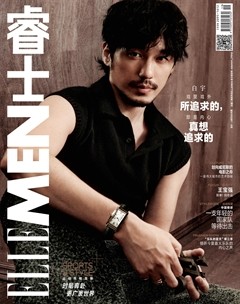1987年,我迈进了大学校门,与操着各式方言,对食堂饭菜有着迥然不同胃口反应的小姑娘和小伙子们团团伙伙成为了同学。四年间,我们纷纷长成了小大人的模样,借助彼此延展开的支脉,大大咧咧地触碰着陌生的世界。
我一定没有记错,班里北京女生肩上的那个小小的白色皮包在我面前仅是轻巧晃过,但依旧让我啧啧称奇。那古旧得恰到好处且残存着一丝洋气的小包上居然有着“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的字样。女生的父亲是电台资深记者,当年曾奔赴伊朗采访过亚运会,这个纪念品十几年后成为了大学生肩上之物,没啥见识但对体育痴迷的我,凭着在《体育报》上读来的各色文章,对此简直羡慕得要死。其实,更准确地说,是对体育记者的职业角色羡慕到了极点,运动会能让我们有机会走得很远,就看你有没有机会出发。
我应该是问过那位女同学,家里还有没有1978年曼谷亚运会的包包,不妨背来看看。好像同学的父亲后来逐渐走上更为重要的岗位,职业航程里也就没有了因为体育的出发与抵达了。上世纪80年代,亚运地位甚高,百姓心中其光芒甚至不逊于奥运,毕竟第一人口大国起点不低,在自己的大洲拿奖牌像是批发进货,升旗奏歌忙不迭。1983年,14岁的我随父亲上街买东西,在一排民居平房的墙上看到一张算是鲜亮的电影海报——《夺标》,招呼大伙儿移步不远的电影院,看看我国运动健儿在一年前的新德里亚运会上的风采。很遗憾,当时觉得几毛钱看个纪录片太不值当,父亲拉着我从影院门前匆匆而过。
我应该是没有记错,《夺标》海报上的主人公是飞越横杆的朱建华,四十一年前在新德里创造的亚洲高度可是2米38呢,荣膺那届亚运会唯一的最佳运动员称号。25岁的张蓉芳身披12号球衣在一张照片的焦点处,46岁的邓若曾清晰可见,那年月她们正当红,当年在秘鲁拿下第二个世界冠军后不到两个月,在亚洲运动会上轻松夺冠。海报置顶处是开幕式时中国代表团入场的照片,虽然红旗遮住了旗手的面颊,但一望便知那是男篮高高帅帅的王立彬,四年后在汉城,依旧是他执旗。若说到旗手,1974年国门刚刚闪开门缝的时代,在德黑兰执旗出场的便是男篮大个子张大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