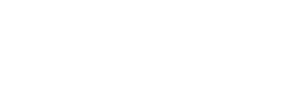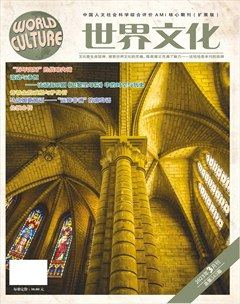《合法副本》(Copie Conforme,又译《原样复制》)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发行于2010年的电影。继《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长生流》《橄榄树下的情人》组成的“村庄三部曲”以及其后的《樱桃的滋味》《随风而逝》等影片后,阿巴斯不仅成为伊朗电影行业的执牛耳者,更是亚洲影坛的一面旗帜。《合法副本》是阿巴斯走出国门、在异国创作环境下拍摄的影片,它不同于阿巴斯以往电影中的本土化视野和聚焦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主题表达,而是将故事背景从偏僻的村庄转移到了充满人文气息的意大利,探讨赝品价值、艺术本真性的问题。
影片讲述了英国作家詹姆斯·米勒来到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为其新作《合法副本》举办新书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他与观众分享了创作的理念,并提到了关于赝品和艺术真实的看法。一个做古董买卖的法国女人带着她的儿子参与了发布会,但中途被儿子打断提前离场。之后,女人和作家在她的古董店再次相遇,并驱车一同前往美术馆,两人在路上围绕“真实”这一话题漫谈。在一个咖啡馆里,女老板错将作家认成女人的丈夫,而两人将错就错,扮演一对结婚15年的夫妻,他们一路上为生活琐事争吵不休,直到最后在宾馆分手。电影时长106分钟,前半段始终在讨论关于艺术真实的问题,即原作和赝品之间是否有差别,以中段作为分割点,从两人自觉扮演起夫妻开始,实现了由物到人的衔接与转变,电影从艺术品的真假问题转换到人物角色的真假问题。
审美特质与艺术价值:赝品合法性之争
本真性(authenticity)和原创性(originality)存在与否,是辨别艺术品真伪的重要价值衡量维度。自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开启了对赝品(forgery)问题的探讨以来,美学、艺术哲学领域始终对如何在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上定义赝品争论不休。赝品的判断维度可分为外部的审美特质和内部的历史价值,强调审美性的形式主义者认为,赝品与真迹在审美维度上是无差别的,艺术品的审美特质仰赖于组织它的各种线条、颜色与结构方式,如果一件赝品能在审美性的感知经验上达到与真迹等同的效果,它就具有了某种合法性。而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对艺术品的判断必须进入历史创造的现场,关注其被谁生产、为何生产、如何生产,这一过程倾注了艺术家独特的个人经验和艺术构思,是具体历史时刻的具体个人的创作意图和感知方式的具体显现,它是一次性、原发性的,同时也是不可替代和反复制的。实际上,赝品的产生并非与艺术真迹同时同步,相反,它是艺术体制及其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出于对创作者和体制本身绝对权威性的保证而生发出的一个对立概念,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并在强调天才、个性与独创的19世纪尤其成为艺术自律语境下的众矢之的,它意味着对本真性、神圣性和原创性的消解,对“艺术作品的‘此时此地’——独一无二地现身于它所在之地”的这一历史过程的省略和抹杀。真品和原作在诞生之时已具有了在时空意义上的独一无二性,因而具备了“光晕”(aura),而赝品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完美,也不能替代原作的历史意义。
在《合法副本》中,电影前半段显然更倾向于形式主义者的观点,即认为赝品与原作不存在审美差异和价值区分。在第一场戏的新书发布会上,作家便借由他的书名《合法副本》说明了他对于艺术真实的看法:“我只想证明复制品本身也有价值,因为复制品引领我们找到原作,认证了它的价值。”“我们一直担心原创性和真伪,从我们祖先到现在始终如一,原创二字对我们而言,有更正面的意涵:真实、纯正、可靠、恒久、具有内在价值,追溯这个词的词源就很有趣了,拉丁文原意是升起或诞生,我尤其喜欢原创一词的诞生之意,我要把这个概念发挥到极致。